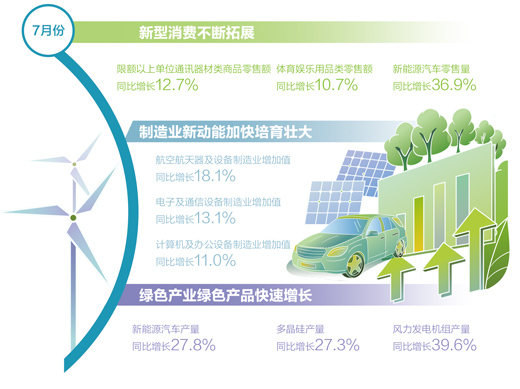来源标题:5年后又见“溜索村”离开大山的女孩们怎么样了?

2020年,“溜索村”全部搬迁完成后,威宁县政府保留了索道,竖立起纪念牌。这是2024年8月14日,新京报记者重返“溜索村”拍摄的镜头。

2019年4月18日,卯会朵背着书包溜索过江。

2024年8月13日,卯会朵在威宁县妇幼保健院做实习护士。

2019年3月24日,卯米会溜索过江上学。

2024年8月14日,卯米会在曾经溜索上学的索道旁留影。

2019年2月25日,刘桂仙从对岸赶集回来,溜索过江回到大石头组。

2024年8月13日,刘桂仙在毕节第三实验高级中学上课。
牛栏江的南岸是贵州省威宁县花果村大石头组,北岸是云南省会泽县耳子山村槽槽组,连通两岸的溜索已存在200多年。溜索距离谷底大约15米,正值枯水期,江上裸露着巨石。
2019年以前,大石头组的村民要想通往外界,必须溜索到对岸。2019年的春天,新京报首席记者陈杰从扶贫干部口中得知花果村大石头组非常贫困后,立刻前往采访报道。
“溜索”对于村里人来说不算难,难的是孩子上学。村里的12个小学生要凌晨4点多打着手电,走四个多小时才到达学校。7个中学生的上学路是只有羚羊才会出没的山路,单程22公里,累计爬升1100米。
报道后不久,由腾讯新闻、新京报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为孩子们发起的助学公益项目“助力孩子最难上学路”就筹款到位。这笔钱用于一对一资助解决19个贫困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等,直至他们高中毕业。
如今,5年过去了,陈杰再次回访当地。曾经采访过的女孩们,有人在医院实习,有人在备战高考,还有人拿了很多奖状。改变的不仅仅是女孩们的命运轨迹,还有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等。“这些女孩如果当初没有走出大山,现在可能都没在读书了”。
女孩“长大了”
在威宁县妇幼保健院见到卯会朵的时候,陈杰一眼就认出了她。虽然她戴着口罩,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
2019年陈杰第一次见到卯会朵的时候,她15岁,读小学六年级,因为9岁才办了户口。陈杰拍了一张她溜索过江的照片,照片里她背着粉色书包,脚蹬一双绣花鞋,两只手环抱住兜套,眼神中有一些茫然,没有看镜头。
在来到威宁县以前,她住在花果村大石头组,距离最近的小学也要凌晨四点起来,步行4个多小时才到。路上会经过泥石流斜坡、巨石间的窄缝、草丛、崖壁,遇到下雨和下雪,路滑加上可能会有石头从山上砸下来,她就无法去学校了。
卯会朵的家离溜索不远,她记得第一次独自溜索的时候,溜到一半不再滑行了,人停在半空中,她需要放开抱紧绳索的手,一点点拉钢索挪到对面。
溜了五六年,他们全家易地搬迁到了县城。那是2019年,卯会朵上学的路程缩短到步行20分钟左右,从小区到学校还有公交车。
在威宁第七小学,班上基本都是易地搬迁来的孩子,但是有不少同学先前的上学之路没有她那么艰难。她感觉到明显的差距,大部分同学的成绩都比她好。临近中考,她征求了老师的意见,报考了威宁中等职业学校学习护理专业。如今在威宁县妇幼保健院,卯会朵已经实习三个月了。
这次见到卯会朵之前,她的沟通能力是陈杰最关心的问题。5年前,他跑了很多次卯会朵的家。她是家里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但不怎么说话。
如今,卯会朵依然是个笑容腼腆的姑娘,说话很轻柔。但也有些许不同,陈杰发现,这个姑娘在聊起内心的想法时,谈吐变得自然大方了。陈杰对旁人说,“确实长大了”。
告别了医院后,陈杰探访了贵州毕节第三实验高级中学,他曾经采访的另一个女孩正在这所学校里念高三。刘桂仙是卯会朵的小学同学,今年18岁。和卯会朵一样,刘桂仙也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她还有两个妹妹,现在一个在重庆一所中专念财经专业二年级,另一个念初二,和父母在昆明。
她和卯会朵有着相似的童年。在大石头组的时候,从家里到学校,爬山累了,上课时会打瞌睡。到家后,刘桂仙还需要帮大人做饭、洗衣服、喂牲畜,忙活到晚上8点,到9点睡觉前,留给她复习功课、写作业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因为路远和糟糕的学习环境,班里很多同学都辍学了。
两年前,她以高出分数线100多分的成绩考上了毕节第三实验高级中学。如果没有搬迁出来,她猜测自己这时也许不是在念书,而是出去打工了。现在,离高考还剩下不到300天,刘桂仙希望能冲一冲二本院校。
重回“溜索村”
在陈杰的邀请下,卯会朵的妹妹、14岁的卯米会和17岁的哥哥卯申文,一起重回“溜索村”。
现在的贵州威宁县花果村大石头组已经无人居住。两个孩子觉得,路没有以前好走了,小草肆意地生长,掩盖了村里的野径,一棵树断了,拦在路中央,田里的苞谷还没有长熟就已经干了。人走了以后,这里重新交给了自然。
在2019年以前,溜索仍是跨越牛栏江的唯一交通工具。这里的溜索历史有200多年,曾经用竹子做的篾索容易断,偶尔会出现死亡事故。20世纪90年代起才换成坚固的钢索,滑轮由木质的换成钢制的,但仍有惊险的事情发生。
一次,一位村干部不小心摔到对面石头上,腰骨折了。还有一次,刘桂仙的爷爷手指放进了滑轮里,还没来得及抽出来就离岸了,等到对岸时,手指没了半截。同去的村干部说,丰水期时激流溅起的浪花能打到溜索人的脚上,让人发怵。
然而,现在溜索不是唯一的过江方式了。据报道,2020年初,一座投资数十万元的钢结构吊桥开始建造,这是大石头组的第一座桥。
故土重游,卯米会和卯申文还是选择了溜索。他们的家就位于距牛栏江约十分钟步程的山坡上,推开门是一个小院子,里头有伙房、牛棚、柴火间、客厅、房间和阁楼等。房顶上是孩子们玩耍的天台,墙上记录着卯米会刚刚认字时歪歪扭扭的笔迹。
哥哥卯申文爬上了更高的台阶,那顶上是一棵核桃树,也是孩子们曾经一起玩耍的地方。眼下果实发青,得再过一阵子才成熟。知道孩子们回老家,父母特意叮嘱他,看看核桃有没有被耗子啃掉。
陈杰第一次听说“溜索村”,是从一个企业的扶贫干部那里。多位干部表示,贵州省最贫困的地方是威宁,威宁最贫困的地方是海拉镇。花果村是海拉镇最贫困的村,其中大石头组所在的“溜索村”,是最艰苦也是最难脱贫的地方。
在2019年拍摄的一段视频里,一位村民背着一筐从别处挖来的土倒在自家院里种土豆。还有一位村民为了喂猪搭配饲料,需要用毛驴运输猪草,一次往返要半天时间。
2019年2月25日,是孩子们开学第一天。凌晨3点,陈杰和两位当地干部起床出发和小学生们会合。大石头组分上寨和下寨,6个孩子在上寨,6个在下寨。5点10分左右,两个寨子的12个学生在大岩山荒田沟谷底集合。他们中最大的是15岁,读六年级,最小的才9岁,读二年级。
陈杰还记得,那天的气温大约在5摄氏度,风力3级,孩子们一起打着手电朝山里走去,他们只穿着毛衣加薄外套,冻得直哆嗦。这样走了4个多小时,8点25分他们抵达终点花果小学。
后来,中学生的上学路,陈杰和同事也走了一遍。这条路更为惊险,从家到学校单程要22公里,累计爬升1100米。中途还要经过一段约7公里、近乎垂直的梯子沟。两边峭壁耸峙,大块岩石裸露在外。因为附近常有羚羊出没,被称之为“羚羊道”。
在此之前,这条艰难的上学路已经存在20年。
好久没回家了,卯申文觉得偶尔远离喧嚣,回来呼吸山野的新鲜空气也挺好的,“释放释放压力”,他说。在卯米会眼里,一些童年回忆永远留在了这里。休息时,她拍了一个视频传给姐姐,里头有对岸的山峦、脚下的牛栏江和裸露的大石头。
想起这些已成记忆中的场景,孩子们不免有些伤感,但一提起上学,他们那时也很茫然。看着身边陆续有同学辍学,女孩们都不知道能坚持到哪一天,也许念完初中就打工去了,卯会朵和刘桂仙都这么想过。
那时的她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变化会来得那么快。
一次命运的转折
陈杰的到来,让这一切有了意外的转折。
在跟随孩子们到达山顶的花果小学后,陈杰发现这里的教育资源也很匮乏。当时学校有一至六年级6个班,但只有5个教室,一年级23个学生挤在大约18平方米的一个小办公室里上课。教学设施陈旧,老瓦房天花板上的墙皮脱落得厉害,随时有可能掉,发现有快要掉下来的,就要提前敲掉。
据资料显示,花果小学建于2006年,三面陡坡环绕,海拔大约在2300米。截至2019年2月25日,花果小学有174名小学生,均居住在周边海拔相对低的山谷或山坡,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家距离学校3公里以上。
要让孩子们的上学路不再艰难,最好的办法是易地搬迁。时任花果村村委会副主任的刘述参,自称是村里第一个走出来的学生,和孩子们有相似的童年经历,他特别希望他们也能走出大山。2017年到2019年,他几乎全泡在村里,劝说乡亲搬迁。
劝说工作困难重重。随着2015年提出的脱贫攻坚战的推进,2017年,大石头组被纳入整体搬迁点。到2019年,全村一半以上已经实施搬迁,还剩下29户,一部分在等待摇号选房,另有10户因各种原因不愿意搬迁,这10个家庭中,有19个学生。
2019年陈杰探访刘桂仙家时,刘述参正在致电三姐妹的父亲,说服他们搬迁到县城,让孩子在更好的环境里读书,但她们的父亲不肯。
眼看劝说无果,陈杰拿起电话询问不搬迁的原因,得到的答案是,就算免费住上了大房子,可是孩子们到了城里,生活开销怎么办?听了这话,陈杰表示理解。在农村,孩子们吃自家家畜家禽的肉和蔬菜就能养活,但是到了城里,一份面条就需要十元左右。刘桂仙的父母在昆明打工,一年一万元左右的收入,需要承担家里七个人的开销,家里的老人还有糖尿病,每天都要打胰岛素。
陈杰又给其他几个家长打电话,得到的答案都是,只要有补助,可以搬。
陈杰想到了腾讯公益,很快就谈成了一个专门为这19个孩子设立的公益项目“助力孩子最难上学路”,并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线上捐款。为了给孩子们更公平的成长机会,他们每人每年可以得到捐助5000元。这笔钱用于一对一资助解决19个贫困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等,直至他们高中毕业。
在“溜索村”系列报道发表后不久,这笔钱就凑齐了。腾讯公益平台的项目页面显示,共有35768名爱心网友参与捐款。正是那年“99公益日”活动的助推,更多有爱的网友第一次知道了“溜索村”的故事,知道了还有一群这样上学的孩子们。
最后的顾虑被打消了,搬迁也很快启动。干部们带村民参观了新家,还有一些易地搬迁来的配套产业,为他们将来就业提供保障。比如在社区里的扶贫车间,会有一些工厂运来原材料,在那里他们可以参加组装的工作,赚取收入。
上医院也变得方便。从前在村里,人们去医院需要溜索,步行两三个小时才能看上病,如今医院就在附近,走几步路就到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社区医生也可以上门看病。
最重要的是孩子们的学习问题也有了解决方案。据当地干部介绍,报道后第三天,贵州省会同省、市、县有关部门人员到现场调研普查海拉镇寄宿情况,对三所小学进行宿舍楼建设和扩建,解决了近千名小学生的寄宿问题。搬迁落实后,孩子们又搬到了威宁县城的第七小学,搬迁耽误了课程的孩子们,也安排了专门的补课。
时任海拉镇分管教育的副镇长孔德亚事后对陈杰说,那篇报道和紧接着的公益项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之前政府做的大量工作已经到了一个难以突破的临界点,就像战争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找到的突破口,与之前的努力形成了合力,共同促成了政策的实施。
陈杰记得孩子们都搬到县城上学后最触动他的一幕:卯会朵家中的老祖母、当时91岁的何莲美抹着眼泪说,“孩子上学不用受苦了”。2020年8月13日,何莲美趴在儿子背上,过了刚建成的新桥。至此,大石头组的最后一家人搬迁完毕。
走出大山的意义
县城里的新家有120平方米,四个房间,两个卫生间,厨房和宽敞明亮的客厅。刚搬进来的时候,卯米会还是扎着俩小辫的9岁小女孩,她睁着充满好奇的眼睛,到处跑跑看看。
隔天,就是卯家三姐弟在县城上学的第一天。早上七点多,他们去往离家大约3公里的威宁第七小学。这所学校有1216人,几乎全是威宁县各个乡镇易地搬迁家庭的子女。到达学校后,三姐弟领取了饭盒、新书包、新校服。
在威宁第七小学上学的第一天,卯会朵就感受到了变化。在这里,老师会讲课本里没有的知识,后来她才知道,这里的老师都是通过各乡镇考试遴选而来的。
如果用另一个角度定义改变,助学项目带来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虽然最后没能念上高中,卯会朵仍觉得走出大山后,她的思想观念变化了不少。比如念护理专业后,身边很多女同学都辍学了,刚开学时班上有60多人,后来只剩下20多人。她能理解那些中途放弃的同学,“许多人感觉念中职没前途,混日子,还不如出去打工”。但她觉得自己不一样,心里总有个念头,要对得起帮助过她的那些人。
孕产保健部的主管护师贺涛理解卯会朵的想法。她当了17年的护士,也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她来自威宁县龙街镇扎塘村,那也是一个边远山区,上学路上需要花费六七个小时,实在走不动时,就搭乘一下恰好路过的拉煤车。
虽然只读了中专,但贺涛已经是整个寨子学历最高的女孩。贺涛告诉陈杰,在威宁县妇幼保健院上班的护士,起码要大专毕业。为此,她常常鼓励卯会朵继续念下去,先考大专,再专升本。
现在,卯会朵会在午饭后和晚饭后花大量的时间学习理论知识,为明年三四月的考试做准备。陈杰觉得,“这说明她有了自我成长的意识,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正是这几年周围环境的变化,才让她看到了成长的机会”。
“看你爸爸妈妈一天天在地里刨泥巴,你们也想这样吗?”卯会朵把当年小学老师在课上讲的话,又传给了妹妹。相比较下来,妹妹的变化更大,也许是因为比姐姐更早接触到更高质量的教学。
家里门上贴着的10张奖状里,其中9张都是属于卯米会的。有“学习之星”“进步奖”,还有实验技能大赛的小学科学一等奖。第一张奖状是小学四年级拿到的语文测试第四名,那一年她刚搬到威宁县第七小学念书。
除了学习成绩,还有其他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卯米会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在陈杰的记忆里,卯米会过去是不大讲究的,头发缠在一起,指甲上都是泥,衣服上也满是油渍,很长时间都没有洗过。
卯米会也在逐渐形成自主意识。在谈话间,卯米会多次提到“重男轻女”的字眼,她认为,即便如此,女孩子读书的成功率还是大一些,“因为女孩更珍惜读书的机会”。
“如果没有走出大山,她们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意识,也许会认为女孩就应该早点嫁人。”陈杰感慨地说。
刘桂仙为了自己的小目标也在努力。搬到县城后,她的学习时间多了一半,但她还是觉得时间不够。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基本都在学习。遇到不会的题,她会打开手机软件求助。她希望可以考上一所211大学,念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后有机会可以去重庆、西藏,还有江南一带看看。在搬出来之前,她没想过,也不敢想这些事。
刘桂仙的班主任李贤介绍,她的成绩离这个目标不算遥远。他观察到这几年发生在这个学生身上的变化,她更乐观,也更努力了。他猜测,也许是对新环境的逐渐适应、同学之间的相互鼓励、老师的认真负责,都让她有了追求梦想的自驱力。
李贤2015年开始在学校任职,完整地带过两届学生,他能明显地感觉到,这9年来,发生在学生们身上的变化。他估算,第一届的大学升学率在40%左右,第二届就升到了60%,他希望刘桂仙所在的这一届能再突破这个纪录。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曾经是一个承诺。然而这些年来,在政府、媒体、社会企业、爱心人士等的共同努力下,它已经逐步成为现实。据教育部披露的数据显示,我国年资助学生人次从2012年的近1.2亿人次,增加到2022年的1.6亿人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已经实现对所有学段、公办民办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全覆盖。
未来也许会变得更好。就像“溜索村”的孩子们,跨过江,才看到更大的世界。